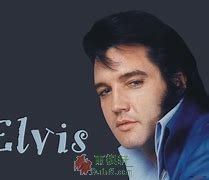亿博娱乐app下载中心 英雄联盟彩票平台排名最新
| 巴兹·鲁赫曼的《猫王》让这个故事的反派成为了叙述者。风中残烛在维加斯城的灯海下孓然摇曳,娓娓道来的回忆近乎是铁锈味的忏悔: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声动梁尘的旋律中,被冰桶和兴奋剂唤醒的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粉墨登场;而经营马戏团出身的帕克上校只满足于宾客的狂欢,用浅笑拧干舞台上那具行尸走肉的最后一丝生命活力。鲁赫曼以登峰造极的华丽视效为电影铺陈了开场,并将自己赤裸的欲望揭露给每一个观众:我要让猫王成为这颗极繁主义烟花的装填物,我要讲述他的悲剧,亦要挥霍他的悲剧——就像帕克上校那样。《猫王》与立传无关,它只用视觉盛宴为传主堆砌出马戏表演式的舞台装置;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只镶嵌着无数枚热情之钻的万花筒,折射出埃尔维斯浮华却又多舛的人生。 我们从帕克上校的视野中所窥视到的故事近乎是以编年体所呈现的:埃尔维斯青涩的初次公演与幼时经历交织呈现,黑人社区豪荡奔放的福音音乐给予他旋律与舞步的启迪,而蓝调之乡比尔街的时尚潮流让小理查德和B.B.King成为了他一生的偶像。前人以美国梦的名义演绎过无数次这样的陈词滥调,鲁赫曼却执着于为自己的版本增添些许华丽的添头。 自出场伊始,小埃尔维斯的形象就与他所钟爱的DC漫画角色,少年神奇队长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赤贫的童年塑造了他的梦想,他期冀录制唱片参加巡演能够让父母告别棚屋陋室,而飞跃永恒之梦便是这一切的浪漫化表达。《猫王》用极端现实却又无比梦幻的方式溯源了摇滚之王的起源,并让这则童话贯彻整部电影始终,即便故事的结局注定会是快乐化作泡影。此番浮夸的诠释恰是最为契合埃尔维斯秉性的切入点,他成为了万千青年的造梦者,却因早逝的母亲无缘见证而抱憾终身;他将豪车和庄园作为礼物赠与路人,一生收集了数量可观的警徽和手枪,并为在主演的电影里看到英雄形象的自己而体会到至高的成就感。埃尔维斯始终是那个出身卑微的男孩,安然浸泡在亲手打造的童话里。他天真地以为周遭世界从此会像触手可得的百事可乐和冰镇香槟一样不竭流淌,直到幻梦溶解消散。 Elvis in Denver Police uniform, 1976也许正是出于对编年体的执着,鲁赫曼将传主的人生切片和那个猫王与之互相成就的年代编织在了一起。非裔社群赋予埃尔维斯的表演以灵魂,被白男乐手弹拨琴弦所支配的主流审美却不能接纳叛逆的音符。为延续传说故事般完美主义的叙事格调,《猫王》摒弃了所有针对埃尔维斯的“盗窃者”指控,将他塑造为虔诚的欣赏者和学徒、黑人音乐家的伙伴与盟友。埃尔维斯与B.B.King、詹姆斯·布朗乃至拳王阿里的情谊自能成为天然的佐证,这堂有关种族隔离史的通俗课程显然也不会止步于此。摇滚乐的叛逆是浑然天成的,在那个上帝、母亲与苹果派是星条旗唯一定义的年代,埃尔维斯乖张的舞步把道德家们脆弱的神经踏得支离破碎。父权和种族主义的化身伊斯特兰德参议员能够轻易打断女儿观看电视上的猫王表演,却无力阻止叛逆新生代在埃尔维斯的浮夸摇摆下肆意释放渴望。 Fats Domino and Elvis Presley in Las Vegas, 1969猫王的神话终究是属于美利坚的神话,他的浪漫情怀与《美国风情画》式的夏日青春图景相呼应,而《无因的反叛》给予了埃尔维斯审视内心的力量。服兵役,邂逅一生挚爱,进军好莱坞,鲁赫曼的猫王编年史看似波澜不惊,就连对抗保守势力的挣扎也被帕克上校精湛的商业手段抚平捏碎。但富足安逸必不能永驻,埃尔维斯的演艺生涯对日渐枯萎的繁荣50年代构成了绝佳隐喻:一部又一部粗劣廉价的甜腻影片透支了世人的热爱,在英伦摇滚入侵和社运风起云涌的新一个十载,马丁·路德·金与罗伯特·肯尼迪的接连遇刺让埃尔维斯对职业生涯的意义第一次产生了颠覆性的思索与怀疑。难怪《猫王与尼克松》中埃尔维斯和总统尽情揶揄披头士之后,也只能悻然为祖国的乐坛辩护道:瞧啊,我们也有帅气的沙滩男孩,有《Good Vibrations》这样的迷幻金曲。 Elvis and Richard Nixon, 1970鲁赫曼安排的答案与之相比显然更胜一筹。1968年的回归电视特辑构成了《猫王》的叙事高潮,埃尔维斯彻底背弃了帕克上校极端逐利的实用主义,一曲撼人心魄的《If I Can Dream》让他的歌声同自由之梦融为一体。鲁赫曼用凌厉的剪辑将民权领袖们的离世与埃尔维斯回归音乐初心的宣言谱成一则驰魂宕魄的蒙太奇,甚至恰到好处地为NBC演播室外走廊墙上的《星际迷航:原初系列》演员群像留足了空间。想象力丰富的埃尔维斯向来热爱有关探索与梦想的故事,他甚至将自己的一匹爱马命名为Star Trek。《原初系列》对种族融合、人类大同的畅想,与埃尔维斯致敬金博士的高歌一并成为了永不磨灭的美国记忆。猫王是美利坚的符号,忠实重现的电视影像击碎了由商业逻辑所堆砌成的明星埃尔维斯,在帕克上校控制欲的废墟中树立起了文化符号埃尔维斯·普雷斯利,无可比拟的摇滚之王。 |
- 相关文章